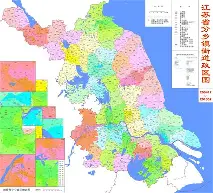比分胶着的第四节忽然变成他的独奏舞台, 每一次变向都像在指挥弦乐, 连续三记不讲理三分划破首钢体育馆的寂静, 最后时刻迎着双人封盖抛射命中, 将沸腾的客队球迷彻底打入冰点。
战局如绷紧的弓弦,在首钢体育馆几乎凝滞的空气里发出危险的嘶鸣,广东与北京,这对宿敌将比分死死咬在92平,计时器上,末节只剩下最后五分钟,体能接近极限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味,每一次对抗都像在泥沼中跋涉,看台上,主队球迷的声浪是翻滚的熔岩,试图吞噬场内的一切杂音,客队替补席前,杜锋双臂抱胸,眉头锁成山川,他知道,需要一道霹雳,劈开这窒息的僵局。
这道霹雳,在下一个回合,携着电光石火而来。
拉梅洛·鲍尔在弧顶接球,防守他的北京队尖兵贴得很紧,仿佛要将他焊在地板上,没有呼叫挡拆,没有多余的晃动,他只是微微沉肩,一个迅疾到几乎模糊的胯下换手,球从右手交到左手,重心随之倾斜——防守者本能地横移,试图封堵,但就在这一瞬,拉梅洛的左手将球轻轻一拉,一个幅度极小却精准到毫厘的背后运球,球又魔术般回到右手,防守者如同被无形的丝线扯动,脚步出现了一刹那的踉跄,就是这一线空隙,拉梅洛拔起,出手。
篮球的弧线又高又飘,在体育馆顶棚惨白的灯光下,像一道逆行的流星。
“唰!”
空心入网,95比92,这声音在骤然一静的场馆里,清脆得有些残忍。
这仿佛是一个开关,北京队的防守,那堵此前坚如磐石的墙,开始出现裂缝,下一回合,拉梅洛借一个单挡掩护,向左横移一步,防守人拼命挤过,手已封到眼前,他完全没有调整,凭借那与生俱来的、近乎随性的节奏感,再次起跳,后仰,出手,篮球划着更陡的抛物线,坠落网心,98比92。
首钢体育馆里的熔岩,温度开始下降,不安的窃窃私语,取代了震耳欲聋的呐喊。

第三个,几乎是镜像重演,对手的扑防已近乎疯狂,指尖几乎蹭到他的睫毛,拉梅洛在空中有一个极细微的挺腰,调整,手腕柔和地一压,球离手的刹那,他已转身,面向客队替补席,伸出三根手指,轻轻点在自己的太阳穴上,眼神平静,甚至带着一丝戏谑的冷感。
篮球在他身后,又一次洞穿网窝,101比94。
“疯了…疯了!”解说席上的声音在颤抖,“拉梅洛·鲍尔!连续三记三分!北京队请求暂停!”
暂停的哨音刺耳,北京队的球员们走回替补席,步履有些沉重,看台上的主队球迷,大多沉默着,少数人仍在嘶吼,但气势已泄了大半,而那一小簇广东球迷所在的角落,爆发出压抑已久的、带着劫后余生般狂喜的呐喊,杜锋依然抱着手臂,但紧锁的眉头悄然松开,他用力拍了拍走下场的拉梅洛的后背,没有说一句话。
暂停回来,北京队发起了最后的、绝望的反扑,他们连追四分,将分差迫近到三分,时间还剩最后28秒,广东队球权,但进攻时间即将走完,球,又一次经过传导,在几乎耗尽24秒时,回到拉梅洛手中,他没有机会冲向篮筐,北京队的两名高大防守者,像两扇骤然闭合的闸门,将他死死封在三分线外右侧的角落。
合围,起跳,四只长臂遮天蔽日,封死了所有传球路线和投篮角度。
没有角度,就创造角度,没有空间,就撕裂空间,拉梅洛在身体向后倾斜、即将失去平衡的瞬间,右手将球高高托起,不是推,不是投,而是一种介于抛射与抚摸之间的奇特手势——手腕极度放松地一抖,球沿着一条诡异的高抛线,越过第一只手掌的指尖,避开第二只手掌的封盖,朝着篮筐飞去。
球在篮筐前沿轻轻一点,顺从地掉了进去,103比98。
时间只剩下11秒,这个进球,抽走了首钢体育馆最后一丝沸腾的能量,那曾经翻滚的、灼热的声浪,瞬间降至冰点,化作一片死寂的、难以置信的冰冷,主队球迷呆立在座位上,有人抱住了头,场边,北京队主帅颓然坐回椅子,闭上了眼睛。

终场哨响,拉梅洛被兴奋的队友淹没,他喘着粗气,汗水浸透了球衣,脸上却没有什么狂喜,只有一种巨大的平静,以及平静之下,如深海暗流般涌动的疲惫与满足,他抬眼,扫过那片此刻已然沉寂的看台,那里曾试图用声音将他埋葬,他转身,走向球员通道,将冰封的球馆和一场被他个人意志彻底扭转的战局,留在了身后。
这个夜晚,最后五分钟的首钢体育馆,名为“团队对抗”的交响乐,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,悄然切换成了独奏模式,而拉梅洛·鲍尔,那位即兴的指挥家,用一连串匪夷所思的音符——两次精灵般的突破分球助攻队友扣篮得手,然后是那三记刀刀见血、彻底扭转气势的三分,最后是那记足以入选赛季最佳镜头的、面对双人封盖的神奇抛射——谱写了一曲专属于他的、狂暴而优雅的末节狂想曲,当曲终人散,记分牌定格,留给对手和这座球馆的,唯有那深入骨髓的寒意,与一个被重新定义的、“关键时刻”的含义。